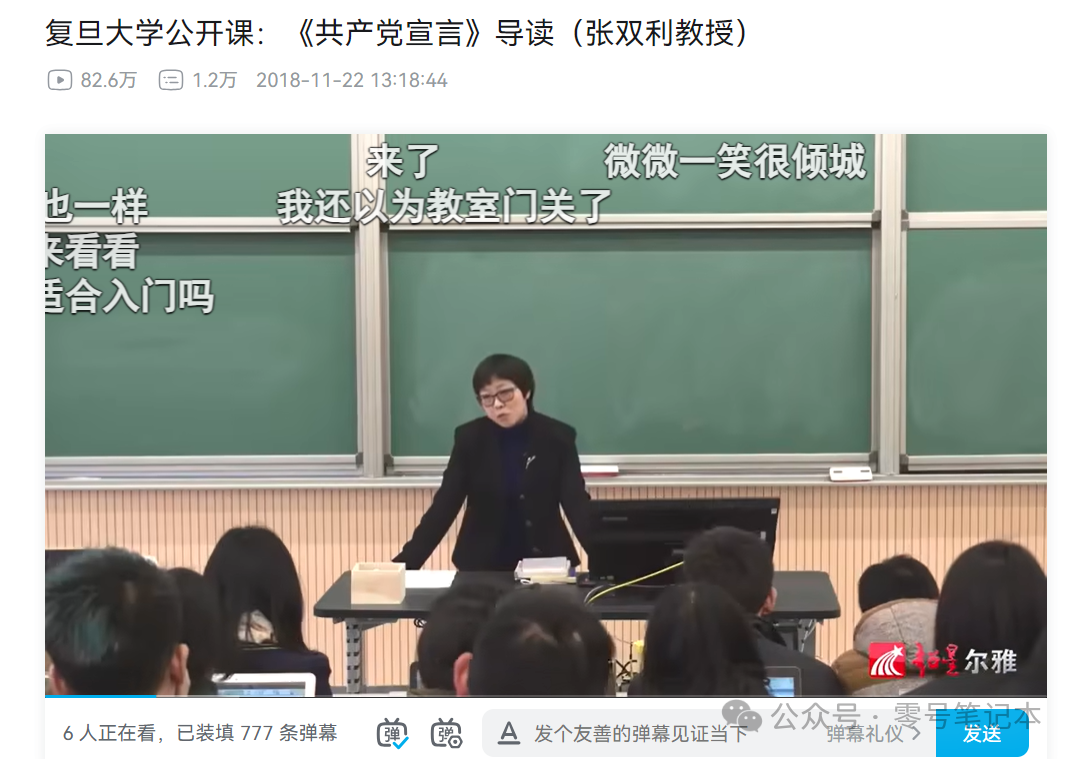【小七访谈】当左翼学生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零号笔记本
主题分类: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工人阶级, 同事们, 旺角, 公司, 理论, 金鱼
涉及行业:
涉及职业:青年学生/职校/实习生
地点: 无
相关议题:无
- 小七通过个人经历和学习,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开始关注工人阶级和劳工权益问题。
- 他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持开放态度,认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应当不断学习理论,通过实践来检验和深化理解。
- 小七提出,城市白领工人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当团结起来关注和争取自身的权益。
- 他关注于不同社群,尤其是女权主义立场上的“同人女”群体,强调在阶级斗争中不能忽视性别等其他重要问题。
- 小七认为,理论学习和实践应该相辅相成,通过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共同探索更有效的实践方式。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文| 江春琦
鸣谢| 小七、旺角金鱼、喵了个咪
“靠,还战斗起来了……”可以说,读者朋友的热情远远超出了临时拉来的两位“编辑部”成员与小七本人的预期。自6月24日发出小七的来信以来,本号先后收到四篇读者的来信讨论,关注用户上涨了将近140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听听小七的想法……”当我把《理论思考是一种疾病吗?》甩到“编辑部”群里时,正准备上夜班的编辑部成员喵了个咪给出了这样的反应。
提议既出,我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读者朋友的表达欲固然值得鼓励,但是我们同样想知道,作为最初提出问题的那个人,大家的讨论是否切合他的疑惑呢?在学习、工作与成长经历当中,他究竟经历了哪些东西才走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拍脑袋想出的项目,是否有长期的生命力?带着这些疑问,我与草草拉来的编辑部成员喵了个咪与旺角金鱼与小七约定了时间,打算线上聊一聊这些问题。
“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其实不是我困惑的点,可能是‘福柯哥’那篇文章歪了楼”,小七直言,虽然大家的讨论很激烈,大家的关注点与他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契合,“在运动的‘低潮期’,我们应该如何行动?”小七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也是从哲学理论开始,工作半年以来,许多经历又为他扫除了些许迷茫:“关于‘怎么办?’的问题,我暂时有一些答案了。”
“最早也是从哲学开始”
在初中阶段,小七有逛贴吧的习惯:“贴吧上有许多‘反建制’的言论。所以我一开始也倾向于觉得‘现实和官方宣传当中的差距居然这么大’但是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还是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就自然而然觉得,如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那我肯定不想要这样的东西。”
他那时恰好迷上了哲学,身边还有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时候基本上看哲学的时候就会去想,我们以后懂得多了就是要努力推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到高中阶段,小七认识了一位影响自己思想转向的关键人物——一位德国柏林大学的留学生。“他参加了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回来之后给我们讲这些东西。然后当时我就想,好像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那么糟糕。”小七认为,如果要反对一个理论,他也应当去认真了解一下它具体在说些什么,“我问他:‘能不能推荐一些东西,让我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于是他推荐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国家与革命》看得小七心潮澎湃:“我靠,我看的热血沸腾,中二之心暴起。原来是这样!他说的太对了!我之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在列宁同志的引领下,小七迅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接触的第一份系统性的学习材料,是复旦大学张双利老师《共产党宣言》的网课。
“那是哪一年?”听见“张双利”三个字,旺角金鱼突然用提问打断了叙述。
“应该是2018-2019年,当时我还在上高中。我当时自学哲学,也正好要学到黑格尔观念论那块,所以其实(网课)都能比较对应的上。然后就发现‘原来马克思那么牛!马克思比黑格尔还牛!’当时的理解就是这么简单。”
“笑死了,2018,-2019年,我也在看双利的网课……”我没有意识到双利即便在复旦校外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看双利网课算什么‘黑历史’吗?”
“我是先自己读了西马的东西才去看双利的西马网课的……当时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有什么西马几巨头,大约是卢卡奇柯尔施还有葛兰西之类的……”喵了个咪也开始插话。
“1819年我坐在教室里听双利讲课……”旺角金鱼似乎心情复杂,“聊到现在最大的感受是自己老了……”
回想起来,小七认为那个时候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最“坚定”的时候。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不由得又开始想,既然这么多思潮都想着要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自己一定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今天去看自由派,可能就觉得自由派很蠢,但是自由派看我们也应如是:‘他们又在信那一套东西了!’”马克思主义真的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方吗?是有更高层次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还是能中国问题给出更好的解答?马克思主义真的能解决当下的问题吗?对他而言,这几朵疑云,时至今日都未能彻底消散。
小七坦言,那个时候他对过去的历史了解非常少,几乎到了无知的地步。面对自由派对苏东剧变的诘问,他似乎很难做出回答:“马克思主义一定会倒向这样的结果吗?一定会倒向极度的官僚主义吗?”从那时开始,这些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小七。他认为,要不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敌相互比较才能决定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回答上面这些问题?如果回答不了,还坚持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不纯粹是“屁股决定脑袋”吗?
从理论上说,困扰着小七最大的两个问题,其一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对《资本论》的一系列批判与质疑,其二是基于黑格尔观念论的那套进步主义在当下社会的完全倒塌:“‘未来会更好’,‘进步历史的大势’,这样的一种观念在今天好像不能被确证了。”不过小七仍然认为,虽然这种历史进步叙事倒塌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问题上的疑惑也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但是与自由派与“小粉红”的那些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还是好上不少:“我去信他们好像就有点太蠢了。他们的理论更没有说服力。‘小粉红’就不说了,他们好像不太需要理论,只需要‘赢赢赢,反对我的都是50w’就行了;不过自由派考虑的就比较‘多’了:他们一方面满脑子好像就只有所谓‘民主’和‘专制’的对立,另一方面谈及现实历史,他们的脑子里又只有‘大人物’的纵横捭阖或者阴谋诡计。既然相信历史由少数人创造,那假惺惺地谈‘民主’做什么?”
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当中,小七最关注的是民族主义和男权的问题。他说,这是因为这些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另外一些理论,比如什么‘施派’,刘小枫,还有什么‘姨学’,这种理论我就不怎么关注了,因为其实没有那么多人买他们的账。”
小七也有自己的理论疑惑:“马克思主义是否还需要一个哲学根基?那套进步主义叙事几乎已经破产了,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哲学基础?但是我又感觉到现实的局面又越来越紧迫,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时候关注哲学问题似乎又是个过于‘书生’的问题。”
“我倒是今天还会看哲学”,旺角金鱼接过话茬,“一方面当然某种意义上说,你去看福柯与阿尔都塞之类的东西,对现实生活未必会有非常直接的意义。有时候往往还会增大自己的痛苦。但是对我来说,它也是一个让我不会完全溶解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方式之一,能维持自己更批判,反思性的思维。”旺角金鱼总结道,“当然这个不能是唯一的方式,不能只靠‘读经’”。
在过去的交流中,喵了个咪非常关注左翼青年的社群生活与媒体偏好。听完小七的讲述,他也将主题转到了这个话题:“现在的左翼青年可能会有另一个共同经验,就是大家或多或少应该都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左翼社群,比如说可能会经常看某些公众号或者b站up主,或者在网上和人交流或者吵架,很多人可能也会加一堆网左群。你能不能讲讲,你接触不同社群,不同思想,运用不同媒体渠道的时候,有哪些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时刻?”
小七迟疑了几秒,继续说道:“我很少进键政群,非常少。我在网上接触的人里,‘同人女’一类的比较多。我感觉她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群体政治化之后,经常会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去排斥‘左男’,会觉得这些人很爹。不知道我这么说你们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小七自认为,与“同人女”群体的交流会让他更关注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不该轻易接受一种阶级还原论——不愿意面对复杂的现实情况,而仅仅是武断地宣布阶级斗争就在一切斗争之前。
“这是一种很傲慢的态度。”
虽然四篇来稿在“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上吵成一团,但是小七却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这么复杂:“你不会一直有事要做,要学理论的话你也总有时间看理论。比如我现在手头就放着一本齐泽克(笑)。”对小七来说,他更希望在工作与生活之中认识一些“积极分子”,认识各行各业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他们形成一些联结,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思考如何能够有进一步实践:“今天你想要一蹴而就的‘整个大的’肯定是比较幼稚的想法。现在只有说自己去学习理论,然后反过来再去实践,实践了之后才能知道自己该学什么,(通过这样的循环)我们的目标就不会变得这么模糊了。”
“城市白领工人应当团结起来”
当小七在谈“现状”的时候,他在谈什么呢?“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是,工厂工人似乎逐渐在大众视野里消失。在很多城市的城区里,你甚至是都是看不到工厂的”。小七出生于山河四省的一个工人家庭,爸爸是货车司机。在他的印象当中,随着“大厦崩塌”,似乎工厂的搬离,工业社区的消失构成了自己所在的城市更真实的历史经验,“我能够看到更多的似乎是城市中的所谓‘白领’们。”不同于传统的制造业工人,“白领”这个词似乎预示着某种更为“优越”的地位。但是对作为程序员的小七来说,这群人似乎并没有他们理论上该有的“体面”:“我周围见到的那些人经常都是早上七点起床,8:30上班,然后一直干到晚上10点才能下班。”
这些人难道不应该团结起来,不应该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当中吗?“我们肯定不能只盯着工厂工人……不能说我们要让所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程序员统统辞了工作进工厂。”小七对这点深信不疑,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认为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存在一些差别。
例如,白领工人似乎更加原子化。他在工作当中观察到,城市白领往往缺乏交流,相互之间也充斥着勾心斗角。而当面对劳资冲突时,他们思考的往往也不是如何联合起来一起与资本家斗争,而是直接辞职,去寻找另一份工作。
作为一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小七从去年10月份开始工作,但是仅仅过了半年,原司就因为企业经营原因开始大规模辞退员工,作为新员工的小七也加入了被裁大军。
小七的第一个公司其实只是一个不到三十人的小公司,公司里也有许多同龄人:“可能大概就是比我大差不多一两岁吧,我和他们也有一些交流,试图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他们当中许多人会在所谓‘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纠结。很多时候,公司要推行一些什么‘改革’,推行一些新规定,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要压榨员工啊。他们就是要降低成本,缓解一下公司的经济问题。“
对于小七来说,公司的种种“改革”自然是“资本家之心,路人皆知”。但是他的同事们却没有那么清醒:“他们会去想,这个政策到底是好政策还是坏政策?”小七对他们的纠结有些摸不着头脑:“你钱少了,怎么还觉得这是好政策?”面对小七的质疑,有些同事认为,虽然他自己的工资变少了,但是这些改革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来看,却又是好的。
“我当时就傻了,这不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吗?”小七这时才发现,原来真的有那么多工人不能够清晰地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
当然了,大家很快就发现“公司的长远发展”与自己没关系了,因为自己被裁了——你把资本家当兄弟,资本家却只会拿你当“代价”。
“很多人其实是实习生。实习生很便宜,但是实习期一过就开始裁员。这件事情让他们大为震撼。他们当时就觉得,公司裁他们的理由都很扯淡,就纯粹是无稽之谈——公司怎么会这么对我?”小七观察到,同事们那种糊涂的“集体主义”思维,在那一刻彻底崩塌了。
作为被裁大军的一员,小七似乎察觉到这是一个行动的机会:“公司当时是批量裁员,然后让大家签自愿离职书。我当时就在钉钉上和大家说这件事,试图拉拢其他被裁的人,和他们说,我们大家一起去讨个说法。”
然而,小七马上就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们要么不理我,要么和我说:‘你哪儿斗得过公司?’然后他们当中很多人就签了自愿离职书。”
小七认为,这次“失败”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是因为我在那边工作的时间不长,也是新员工,也没有多大的威信,大家就不会听我的。第二是因为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考虑,比如就会觉得‘我要交房租,如果要陪你在这里和公司搞一个月,我下个月房租怎么办?下个月其他吃穿怎么办?如果时间拖得再长,我耗的不是我接下来挣钱的时间吗?’有人也会和我说这些东西,他们也会很焦虑,我现在想想其实他们也是有自己的道理的。”
“不过,其实他们把公司想得太厉害了。我后来的经历证明,其实公司也没那么难斗。”小七咨询了两个职场老油条,最终决定不签自愿离职,去找劳动监察大队争一争补偿金。
“当时想了好久,该什么时候去,怎么和劳监的人说,多少还是有点没底……” 小七坦言,第一次“阶级斗争”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压力,“中间有一天,我晚上还梦见阳和平和我说,要我好好去投诉。醒来才发现,昨晚手机上b站没关,一直在放阳和平的视频……”
拖了将近一个月后,公司才在补偿金的问题上松口。“其实补偿金也没给全,应该给半个月工资,但实际给我的根本不到半个月。但是我也的确没有心思去接着走仲裁了,因为如果要为了那2000块钱走仲裁,还要再拖下去,太累了。”虽然没有发足补偿金,但是小七同样觉得这是一场胜利,“我当时想的是,能要到钱就是好的,就算是胜利了。我可以给剩下的员工看看,其实公司没什么可怕的,我能要到的钱你们也能要到!”
去公司拿补偿金的那天,小七非常风光地跑去工作区,向同事们宣布了自己的胜利:“那天的事情我感觉很棒,应该也挺给他们鼓舞的。当然公司大裁员没有把所有人的裁掉,但是其他人应该也多少有些‘危机感’。之前他们都一直和我说‘别搞了,你怎么搞得过公司’,但是这事儿之后,他们也会在微信上和我说,之后如果出什么事儿,他们也想和老板争一争,希望之后我能帮帮他们。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现象。”
除了这次“斗争”经历之外,小七还对公司内不同部门的矛盾印象深刻。首当其冲的就是人事:“那个狗人事!其实上一任人事是和我一起被裁掉的,她自己是新招进来的。就这样,她还搁那儿帮着老板裁员?帮着公司阻止我来要补偿金?我就记得她对我说:‘你看着这么好个人,怎么干这种事?’当时都给我气乐了,好人就该被拿枪指着?”
当然,小七也知道人事的尴尬境地:“如果她在这件事情上要帮我对付公司,估计她就要被裁了,但是如果帮公司,未来如果她自己要被裁的话,又该怎么办?有人愿意帮她吗?”
“新招的人事往往会更卖力地帮老板,” 旺角金鱼插了一句,“因为ta刚刚得到这份工作,肯定要更卖力地去展示自己的‘工作能力’。从岗位设置上,人事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位置。一方面你是一个打工人,但是你的工作内容就是和老板统一战线,对付工人。”
除了人事之外,公司的技术部与销售部之间也有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小七的回忆(小七作为程序员属于技术部),在那家公司,经常能听见技术部的同事在怒斥销售部的人,每次销售部的人来到技术部,也没什么好脸色。他和同事们在一起吃饭时,公司的老技术员还会和他说:“看见那个销售部的XXX了吗?你们离他远点儿,少跟他接触,他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
“这么个公司才不到30个人,这么一搞至少一半的工人就被划拉开了。未来有啥事儿如果真要搞团结,想想就挺难的。”公司的部门划分使得企业员工内部就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由此也让员工之间的矛盾在日常工作当中就积攒起来。
在旺角金鱼看来,大部分公司都会有这类情况:“因为市场销售本身就是销量导向的,有销量的前提就是你得有好产品,所以你就必须对技术或者产品部门提要求。很多时候市场部门不懂产品,就容易提出脱离技术实践,或者对产品部门压力非常大的要求。所以在企业日常运营当中,二者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像互联网企业经常传出‘产品经理逼疯码农’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
“是啊,但是互联网企业还有个懂技术的产品经理做技术和销售之间的中介,已经比我那个公司好太多了。“小七发出一声感叹,“但是即便如此,这个矛盾还是在那里。所以我就更容易去想,在城市白领当中去搞组织和团结,这是一个难点。”
喵了个咪认为小七区分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理由不太充分:“之前你提到城市白领工人可能生活更原子化,更个人化,但是在我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我观察到的产业工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和其他所有在上班的人都一样,其实都是会很优先个人化地看待利益问题。他们也不会自发的去搞串联或者团结起来。我觉得如果是个人化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个普遍特征。”
“嗯,我没有进过厂,所以其实不太清楚工厂里是什么样。”小七想了想说,“只是从我看到的材料来说,好像工厂更容易出现那种群体性的活动,但是城市工人里似乎就不太容易。比如某些互联网企业,似乎就算是非常大批量的裁员,他们往往也是领了补偿金就走了,不过可能是因为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另一方面,好像许多城市工人都已经被逼到跳楼自杀这种情况了,他们怎么还不会想着说可以联合起来去跟老板干一仗?从这个现象上,我会想,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是不是有区别?但是这个区别是不是真的存在,其实我不确定。”
旺角金鱼认为,小七观察到的现象,是因为当事人尚未看到另一种可能:“当然有人会说,在面对这些不公和压力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联合起来,可以这样那样。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个选项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念上,而必须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实践性的东西,让人觉得‘这么做是有戏的’。我觉得这点不管是对包括码农在内的白领工人,对车间里的产业工人也是这样。我们谈团结,不能仅仅是在喝酒吹水意义上的谈团结,而是得有具体的,摸得到的东西。
比如在这件事上,面对被裁,你是选择签掉自离,还是鼓动大家一起去要一个赔偿?最关键的是当事人的世界观里需要有这样一个选项,认为某种意义上的行动,尤其是集体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在今天的很多情况下,无论哪里的劳动者都看不到这种可能。所以最好的局面可能只不过是拿钱走人。被逼到墙角,可能就只能选择某些‘极端手段’。”
“对!”小七立刻表现出赞同。
旺角金鱼认为,自己的回答是最简单,最宽泛的。但是如果进一步问,如何能向大家提交这些选项?平时要如何去做这些工作?这个问题或许就是之前小七提到的,在“现状紧迫”的情形下,该关注那些理论问题?
“这时候可能就得去学习和思考一下白领工人,或者更具体的,程序员的特点是什么?就像喵了个咪说的,我们看到一些现象,觉得这些现象需要去反思,这时候这些问题会成为理论工作的起点。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同事们建立关系,搞好联结,这个是我们工作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在理论上理解和分析不同人群的特点,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重要的。”
在制造业工厂工作的喵了个咪认为,小七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是产业工人群体遇到的问题:“我感觉小七提到的同事们的状态,就是大部分平常劳动者的状态。大家的思维底色都是一样的。然后大家的遭遇也差不多。工厂里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推行各种‘新规’,包括薪资拖欠等等,这些都是每个打工者普遍遇到的问题。工人的心态和小七的同事们没啥分别。”
“我个人觉得,争取离职补偿作为一个起步的斗争,其实非常合适。很难在工作场域找到比这个议题还合适的东西了。”旺角金鱼有感而发,“我们都知道签不签自离,那就是白花花的银子的差别。反正都要被裁了,你不签字其实公司也未必能奈何得了你。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坚持斗争,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这个问题上,旺角金鱼反而比较好奇,为什么其他被裁员的同事很爽快地签字走人?
“大家会衡量成本收益。”小七解释道,“比如有人会认为反正都要走了,签了就签了,无所谓。不签的话你还要和公司去拖,要去花精力和时间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最后得到的收益可能还不如我马上找第二份工作,拿到的钱可能比补偿金还多。另外一些老员工还得考虑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所以他们就算这样被裁了,自己很生气,但是也会觉得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和公司斗,争取这些东西。”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工厂里的工人也差不多。”,喵了个咪随口补充。
“后面的四篇来稿我都看了”
“后面四篇来稿我都看了……我觉得‘福柯哥’那篇最气人,对我的情绪影响最大。”
“为啥影响情绪?”
“他的文字太形象了,我都能想象到他的语气神态是什么样的。我能马上对上那些平时在各种群里也好,网站上也好看到的那种人。什么‘二十岁的福音’,不就是说年轻人才会信马克思主义,‘长大了还是左派就是没脑子’这种话?他还在那边讲什么马克斯·韦伯,最后还让我去多看福柯……气死我了,那种爱指点江山的‘爹’的形象马上就凸显出来了。”
小七认为,后面三篇文章写得都还不错:“我自己也是从看哲学开始(左转)的,再加上在今天,其实‘网左’和‘网哲’两个群体其实非常重合。”
小七认为抽象地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不够的——我们自然可以说“理论可以反过来影响实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些理论问题更靠近大家的困惑,但是另一些就未必:“比如我们如果去研究白领工人,他们为什么不能形成一种阶级意识或者另外一些关于改变自身处境的想象?这个问题与实践中的困惑是相关的。但是另一些问题,尤其是许多哲学层面的内容似乎就不能那么靠近大家现实当中的困惑。比如我们讨论一些本体论的问题,我也觉得这些问题很有意思,某种意义上我也不会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但是确实离那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远了一些。”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试图总结,“理论话语可以晦涩,也可以直白,但是理论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是否重要或者迫切,是非常关键的。比如你关心城市工人,如果有个理论能回应你的困惑,并且教你怎么做,那我想就算晦涩一点,我们也愿意去学。但是如果你用一堆晦涩的修辞,最后讨论的是一个绝大部分读者都觉得无关紧要的话题,那就活该被人嫌弃。”
“第四篇文章提到,很多‘左派’似乎都在cosplay?”小七接着说,“我记得他提到,很多人是在理论上有共鸣,但是在一些非理论的层次,是没有行动空间和纽带的。因此大家才会转而去过度地讨论理论问题?”
小七对此有些疑虑:“我观察到好多在理论上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脱离学校进入社会之后,马上就变得非常非常保守,和他们之前在学校里那副样貌完全不一样。”
小七身边就出现过这样的人:“在学校里的时候,他一直在写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文章,在键政群里办报纸。我不评价他写的东西怎样,但是他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出现的。但是他毕业工作之后,马上就变了一个人……他开始变得极端保守,极端自大。天天把‘小仙女’,‘尼哥’这种词挂在嘴边,变成一个十足的男权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
小七回忆起有一次与这位过去的“进步学生”在外边散步。路上看到了拆迁留下的残垣断壁,上面还写着“还百姓拆房钱”、“还百姓命根子”之类的标语。这位“进步青年”看了一眼,只是幽幽地叹了口气,用一种非常悲悯的语气说:“总得有人要牺牲的。”
那一刻,小七只感觉恶心。过去他的所有姿态都显得尤为虚伪:“他以前是那种三句离不开‘阶级斗争’的人,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因为历史原因,我们国家的左派话语与保守主义之间有着复杂的纠葛……”旺角金鱼认为这个现象也未必能还原为“空谈理论”的恶果,“比如谈及革命史的时候,很多人自然而然的会说:‘革命先烈的牺牲铸造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但是很不巧的是,最爱这句话的恐怕是那些躺在先辈功劳簿上的‘二代’们。”
在同一篇文章里,小七还关注到了文中提到的工人精神健康问题:“他有提到,有些人认为抑郁症是一种‘富贵病’,工人很忙,所以没精力去抑郁。其实这一段我找我的朋友讨论过,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工人自杀率很高’。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在工人处理精神问题的时候不是很习惯用抑郁症的话语?”
“我觉得这倒不至于……”喵了个咪回应到,“在我那个厂里,还是会有工人聊抑郁症话题的。他们也会在厂里问,自己有个朋友抑郁了,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工友会来问我的意见,如果这个东西需要治疗的话,应该去哪里,怎么走流程,有什么注意事项?作为朋友的话,应当如何去更科学地去和存在心理问题困扰的友人沟通?不少工友会问这些很具体的问题,也有一些工友会来问我抑郁症本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怎样去‘预防?’其实心理学话语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了,工人自己天天刷抖音也能刷到,所以今天的工人还是多多少少会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
“所以其实心理学的‘科学话语’也一直在进步,”旺角金鱼接过话茬,“21世纪初,农民自杀问题曾经广受关注,在很多这种案例中可能小七提到的现象——对‘抑郁症’缺乏甚至没有认知——是存在的。但是新一代/第二代农民工无论是接受的教育还是接触的网络环境,都已经很不一样了。”
但是,旺角金鱼与喵了个咪都认为,虽然抑郁症作为一个相对客观的病症是普遍化的,每个阶级内部都有可能会存在,但是中产群体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垄断一种“典型的抑郁姿态”。一方面,那些对抑郁症的知识与经验的叙述,传播与想象又往往会给读者预设一个中产阶级的形象;另一方面,从心理学临床资源来说,不同群体自然是存在着不平等的。
“比如像中学大学里需要配备心理老师或者心理咨询师似乎已经是一个共识了,”旺角金鱼突然开了个脑洞,“但是至少在国内,好像很少会有人想象制造业工厂里应该去配备心理咨询师。”
经过讨论,大家马上意识到其中的困难:其一,如果工厂配一个心理咨询室,工人大概是不愿意进去的——如果厂里知道我有心理问题,会不会直接把我开了?其二,制造业工厂往往不会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工人只是螺丝钉罢了,不好用就换人,反正“你干不了有得是人可以干”,资本家自然没必要花功夫搞这些。
小七认同这篇文章对这种现象的批判。他身边就有人觉得只有那些家里“有钱有闲”的人才会有精力去弄什么抑郁症,觉得抑郁症是“小资产阶级病”。然而比较可笑的是,一般指责抑郁症患者“有钱有闲”的这些人,还真的是那种家境富裕,家庭环境美满的那批人。
“那就正常了。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个阶层的人,所以只见过‘有钱有闲’的病患,家里没钱的抑郁症患者根本不会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
结语:如何行动才不算是“等待革命?”
“我对这个项目的期待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想多认识点能线下见面深聊的朋友,但是这点似乎又有许多技术上的障碍;第二点是看了四篇文章才想到的。能让大家‘有感而发’,积极投稿,也是好的。”谈及对读者来信环节的期望,小七这么说。
不过在小七看来,大家讨论的话题与自己最初抱有的“总问题”有一定差异:“这么说吧,我感受到,经济下行趋势越来越明显,形势也越来越紧迫了,但是‘高潮’又没有来。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怎么做才不算在‘等待革命’?”
“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想法是要避免两种心态。一方面是拒绝一种自大狂的态度,认为我一个人就能带动历史,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具体来说就是别妄想着说我要马上搞个‘大的’。另一种就是纯粹的一边工作,一边‘做做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生活泾渭分明的切割开。当遇到现实问题的时候,还是以一种原子化的姿态去面对。我会认为这种就是‘等待革命’的表现。”
“那你的‘版本答案’是什么呢?”听完小七叙述,旺角金鱼问出了大家都关心的话题。
“我们需要去探一探,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到底能做到哪一步?对我来说,一方面是在行动上建立联结,努力打破今天打工人原子化的局面:我的事并不只是我个人的事儿,这次我一个人去要赔偿,下次能不能多两三个人一起去要?这些经验和支持能不能传递下来?能不能帮助,团结到更多的人?另一方面是用理论的眼光去审视自己的各种经历,并回过头去修正自己实践当中积累的经验。比如今天我在讨论当中知道产业工人对抑郁症没有那么排斥,那以后我遇到相关的事情,我是不是就多了一些思路?简而言之,如果我们认定了我们是这样一个历史趋势的一部分,我们就必须积极地去推进它。”
公共社会科学小组联系邮箱:
欢迎热心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