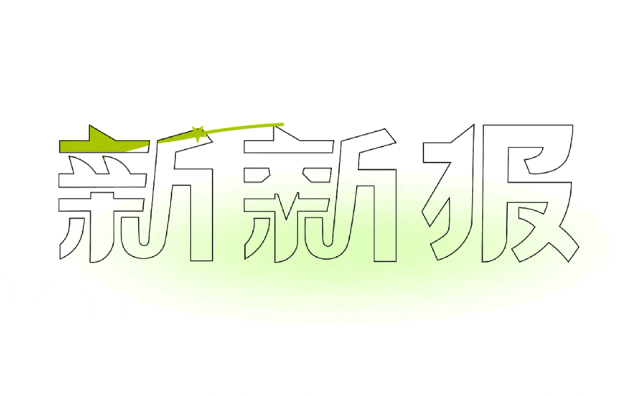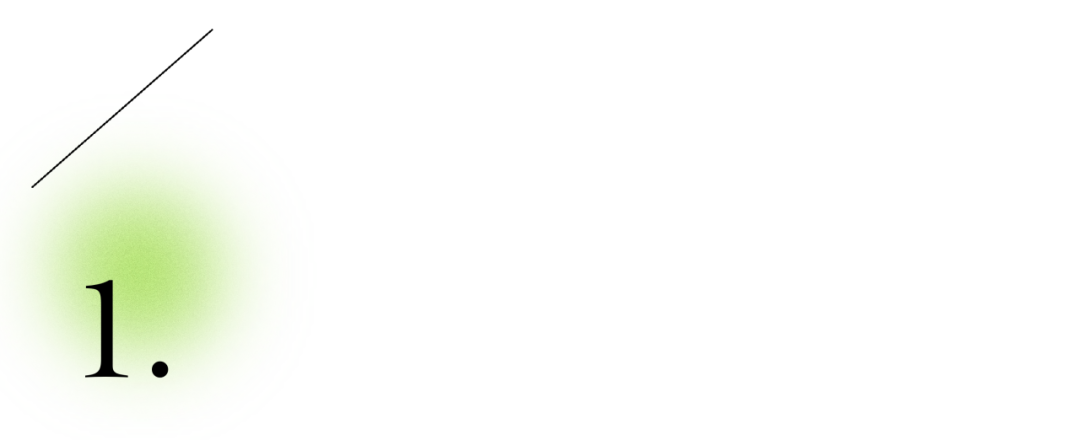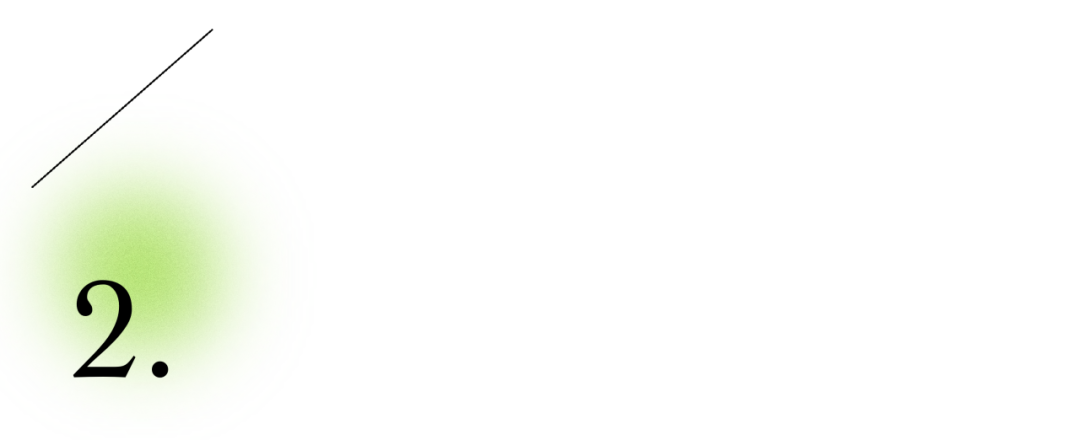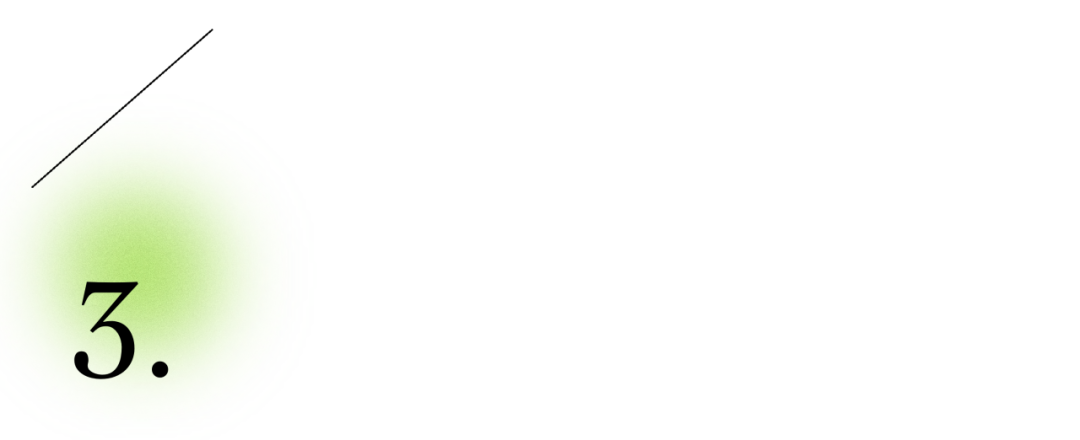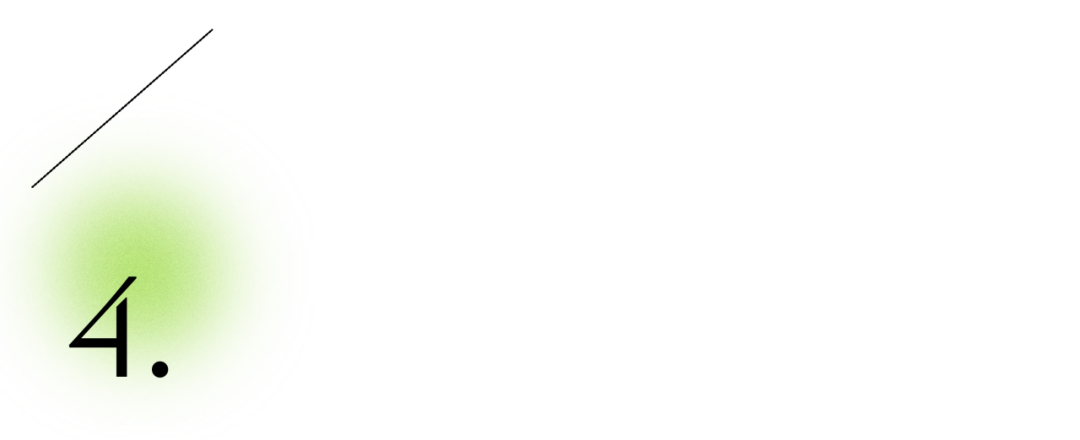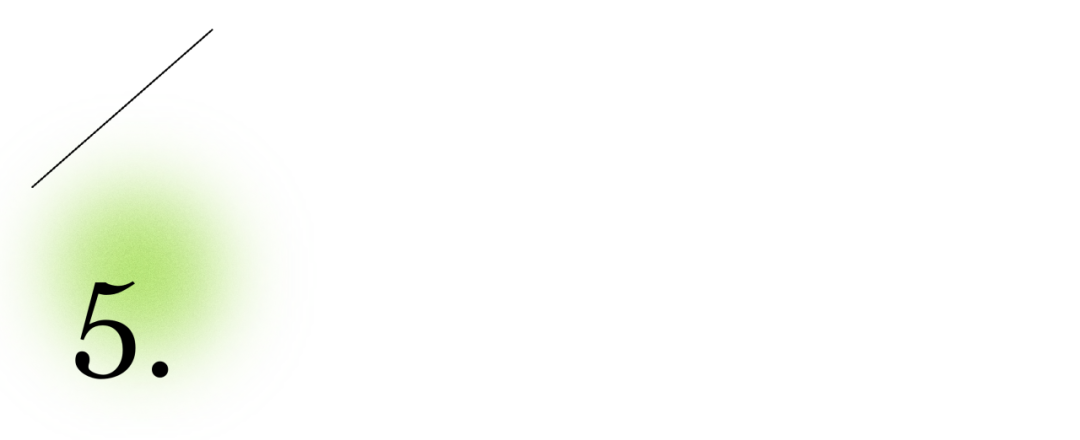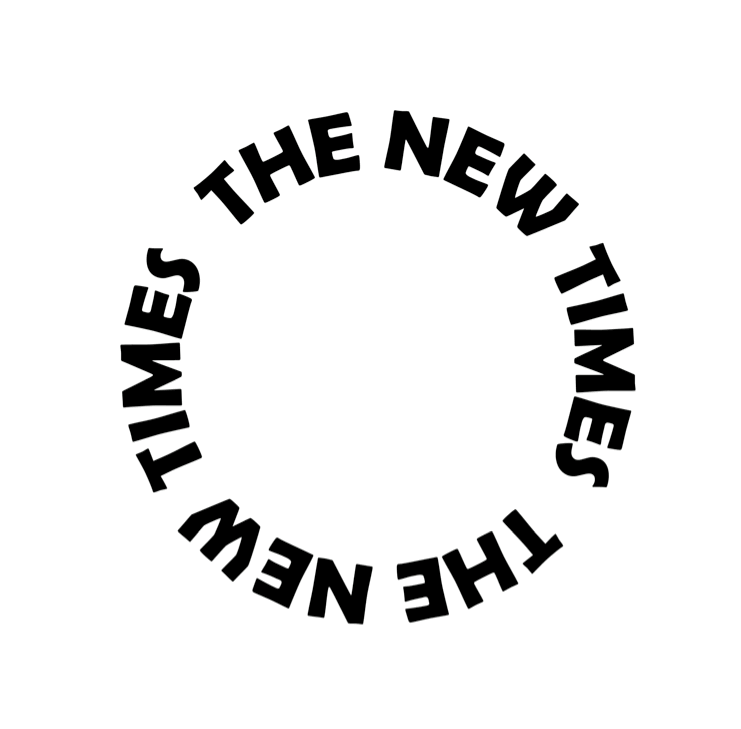【2020级新闻毕设】她立于瓦砾之中 融不进的城市,工地女性的“无稽之谈”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新新报NewTimes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工地, 深圳, 女儿, 塔吊, 老家
涉及行业:建筑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广东省
相关议题:无
- 工地女性作为一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她们在传统女性角色和渴望自我独立之间承担着双重责任和辛苦。
- 曾立新和其他工地女性通过辛勤劳动,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中寻求生计,尽管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生活的不适应。
- 工地女工在家庭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赚钱养家,但工资并不高,且职业选择受限。
- 在深圳这样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工地女工见证了城市建设的每一步,但她们的劳动和贡献往往不为人所见。
- 工地女工在追求自我价值和生活改善的同时,面临着职业安全、健康和社会认同等多重挑战。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提到工地,人们脑海里或许会浮现烈日下汗流浃背的搬运工,青纱外踩着吊板的高空作业工人,但这些形象往往都是男性,工地女工藏在工作服、安全帽里,隐在社会关注的聚光灯外。工地不需要高文化,出卖力气和时间就能换来养家糊口的钱,是很多女性农民工的“优选”。
工地女性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顺应传统女性角色中结婚生子的程序,但在知识技术有限的前提下却又是渴望着自我独立的个体,双重责任,双倍辛苦,她们创造出了一种鲜活的,独一无二的生命历程。
我们疑惑着,她们为什么选择深圳?她们有着怎样的生命历程,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如何选择?她们和深圳的链接体现在哪里?链接的程度是怎样的?
这些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女性农民工们的故事是充满挑战和希望的。我们走进深圳龙华某工地,采访了4名工地塔吊指挥员,2名电梯驾驶员,下面是她们的故事——
文字 | 陈书婉
编辑 | 武子婷 曾菲彤 陈书婉 贺思雨
指导老师 | 陈显玲 周裕琼
点击观看新闻纪录片——《她于瓦砾之中》
“需要多少人间灰尘才能掩盖住一个女子,
血肉模糊却依然发出光芒的情意。”
“所有的建筑
都充满了钱的味道”
2017年5月,36岁的曾立新刚出深圳北站,一股热浪把她从浑浑噩噩的七小时路程中拽到现实。热,好热,这是她对深圳的第一印象。
三个月前, 她第一次跨省出远门,从云南曲靖的农村到浙江温州的电子厂打工。“电子厂很枯燥的”,工作任务是给充电宝装配件。她每天在望不到头的传送带旁站着,重复拿取这一个动作,上完名义上的白班,下午又收到工头的通知,接着上夜班,一天要连做12小时。
曾立新这时刚出月子,二孩出生后她不想继续在家种地,而厂里如此强度的工作让她身体眩晕头疼。第一个月到手的工资是3600元,第二个月3700元,之后再没有增长,只求不扣钱。“上厕所要先打报告,没轮到你就憋着,擅自离岗就扣钱。”
她离开了工厂,坐上去深圳的动车。大姐夫给她介绍了工地的工作,她跟大姐、二姐和丈夫一并来这里,出门在外总有个依靠,她想着。曾立新丈夫做搬运工,她帮忙打下手做杂工。后来自己一个人做塔吊指挥员。工地也很累,但一天只上9个小时班,“工地也累,但自由些”。
曾立新接受采访中/记者拍摄
刚来深圳的这一年,曾立新觉得什么都好新鲜。路边的树又高又直,不像老家的矮矮的铁树;每天都跟火炉一样热,吃的东西清淡没味,前一天吃了些辣的第二天脸上就长痘了。跟云南一点都不一样。今年是她在深圳的第八个年头,曾立新仍旧很不适应。
工地上的老乡跟她说,深圳的地标建筑就是“跨江大桥”,桥对面就是香港喽。趁着刚进工地不太忙,曾立新夫妻拉着姐姐姐夫,还有工地认识的一对夫妻,八个人周末的时候去爬了大南山。
一行人爬上了大南山的顶峰,深圳湾大桥就在远处。原来大桥跨的不是江,是海。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海,在此之前她连洱海这个大湖都没见过。旁边人跟他们说,过了这个桥就是香港了。他们在那里看了又看,拍了照又跑到公园最能靠近海和大桥的地方。
香港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一直和善跟我们聊天的曾立新坐在铺得整齐的床边,“哎呦,对我们这些人啊,”她突然笑出声,不自觉提高了些音量,人往床帘遮住的床头微倒,“就是无稽之谈噢。”
深圳湾大桥/图源网络
同样是2017年,曾立新现在的室友李七双的二胎也出生了。她辞掉了待了四年的深圳食品厂的工作,回到云南弥渡县的老家备胎生产带孩子。
从她20岁结婚起,她和她老公一直是在一起的,不管是两人在大儿子2岁的时候一起外出打工,还是怀了二胎回老家。小两口在家的时候,公公婆婆就外出打工,四人轮流着打工和守家的职位。两位老人第二次外出打工时,已经是60多岁了。
李七双在繁冗的生活中想喘口气的时候,就会给在深圳食品厂工作的好姐妹打电话聊天。食品厂的工作确实无趣,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地喧叫,但她一直怀念着那里的生活,这些好姐妹让她在陌生的城市感受到互相依靠。
“在家待了一年,该出去了。”李七双和老公商量后,和两位老人又一次交换了家庭生计的担子,2018年,她重返深圳。在朋友的介绍下,李七双考了塔吊指挥员的证,开始了工地生活。
距离现在工地三四公里外是一个学校,那是李七双的上一个工地。每次经过的时候,她都好自豪,“干我们这个活,看着房子一点点搭起来,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
搭住房建筑的时候,售楼处在楼没盖好前就建好了,房子一边建,售楼处一边卖。她每天指挥塔吊的时候,看着材料在空中平移、升起落下,在工人肩上扛起又放下,会想:“这些东西今天搭的厕所,卖几十万,一套房子几千万,“深圳真是有钱人的地方,所有的建筑都充满了钱的味道。”
“自己赚钱自己花”
这个工地目前1000多名工人,只有10名左右的女工,集中分布在电梯工、塔吊指挥员这两块,工资是工种中较低的,只有一个开塔吊的女司机。由于男女生理特征差异、市场用人自上而下的考量、工人个人选择等原因,工地女工数量少、职业分布集中。
工地负责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一是女性身体吃不消,一般都倾向选择轻松的活;二是男性一般占家庭经济支柱的地位,高空工作、重体力活工资较高,男性更愿意做,市场也更倾向于他们。
女工背井离乡打工挣的钱,在家庭经济中占据怎样的分量?她们是分配自己的工资的?
左正秋今年48岁,已经做了9年的塔吊指挥员。她个子不高,但能看得出是能够经得住辛苦的体型;脸圆圆的,皮肤很好,交谈的时候,聊得尽兴了,能看到透出的红晕。我们初见她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她的女儿已经26岁,儿子25岁了。
6点下班后,左正秋从食堂打了饭回宿舍,两荤一素,开了一盒豆豉鱼罐头当小菜。工地木匠用木板和螺丝钉起来的桌子有些矮,左正秋坐在塑料红椅子上,弓着背边吃边跟我们聊天。
一个男工老乡进门就拿了个板凳坐左正秋姐旁边,他熟稔地抓一把桌上的瓜子,屋子里顿时充满了热情的四川方言,“这个鱼罐头放不住的,会臭,要一顿吃完。”左正秋正拿塑料袋包起没吃完的鱼罐头,听到话动作也没停,“能放,像我这么斯文的人一顿吃不了两条鱼。”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该省省,该花花。左正秋经常说起这话。她的孩子都已独立,几年前她给在部队的儿子全款买了房。现在一个月6000元左右的工资,“自己赚钱自己花很舒服。”
曾立新的回答和左正秋如出一辙:“自己挣钱自己花,靠别人都是靠不住的。”她说,老公是养全家,她要做的是自己养活自己。
“我没有刻意省吃俭用,就正常花。”而曾立新的日常开销就是吃饭,几乎都是食堂吃;偶尔去工地外面吃点好的“犒劳自己”,八十多块钱点两个小炒菜;工资剩下的钱就往家里寄。
同样的工资,曾立新还有个尚在初中的小儿子需要养活。聊天的时候,她穿着紫色的短袖,眼角被太阳晒得有些发红,常年被紫外线晒得有些黑的脸上亮着刚涂完护肤品的水光。在深圳的三年,她很熟悉网购了,“身上穿的这件吗?不下工地,我会在网上买耐脏耐穿的衣服干活穿。”
她刚从超市回来,白色塑料袋封着各式的蔬菜和水果,放在一个比A4纸大点的储物篮里,床铺上面放着饼干面包这些抗饿的零食。
30平米的宿舍,平摊到每个人就只有床底、上下床的上铺和床头的一个板凳面积能够放东西。所以她们买东西克制着囤货的习惯,每次只买一点点,而这些东西就花了曾立新200多块钱。
每到这时候,她总是会怀念云南老家按公斤秤的瓜果。
微弱的深圳痕迹
“我单身,嘘。”常秀梅凑近我们小声地说,害怕被旁边的工友听到。常秀梅的女儿在深圳当护士,她跟着女儿来深圳找了份工作。
深圳很多老年女性都是相似的情况,跟着儿女到了深圳,给自己挣一份养老钱。今年49岁的常秀梅不想因为自己的婚姻状况遭受可能的议论,在工地一直很沉默。在老乡介绍下,她去年3月在这个工地上做电梯驾驶员。
常秀梅在抖音有6000多个粉丝,个人简介写着“照片小影视分享博主”。她会发自拍、抖音特效变脸、拍自己唱歌跳舞的视频分享自己工地生活的视频,一天能发四五条分享日常,每条抖音都会加上实时定位。
3月30日,常秀梅发了个跳舞视频,配上《做一个美梦》的卡点曲,跟着曲子对嘴型。她穿着蓝色工人马甲,跳舞地点就是那四平米的红色电梯。这是她的工作区,也是她的舞台。
但她的朋友圈只有不加配文的微信视频号转发,都是些搞笑视频。“我喜欢拍视频啊,但不想直接让工友看到。”
同一个寝室的杨承兰也爱发抖音,拍个日常工作视频之类的。但在工地上,除了和自己的亲妹妹杨承银聊聊天,很少和其他人有深交。她不知道微信的屏蔽功能,也不愿意捣鼓,索性不发朋友圈了。
她们如此平淡又珍惜地过着每一天的生活,会费劲地给自己的视频配音乐再发布到社交媒体。而在朋友圈这样熟人领域,又是另一幅景象。
左正秋的朋友圈仅三天可见,头像是一棵草。我们加了她的一个月时间里,她从未发过动态,“我几乎不发,”她坦白。
她的丈夫在另一个城市打工,女儿知道她一个人深圳有些不放心,经常跟她通话。她们会聊最近的情况,“但我从来报喜不报忧,对父母对孩子都是这样。”在工地难免会有摩擦,左正秋懊恼起来会自己偷偷哭,甚至扇自己,但从不跟任何人倾诉。“在外面有事情自己处理,我自己能扛的。”
李七双的朋友圈数量一年年减少,去年只发了3条。她会发自己的自拍;丧气时,会发个“鬼火冒”的怒气表情包,配文“都是些神经病”;在云南的树林里,一双儿女依偎在她的两肩,亲昵的照片:“宝贝,对不起。妈妈要踏上打工的路途”……这片她精心布置的情感自留地里,没有深圳的痕迹,又好像处处都有深圳。
李七双和她的孩子们/图源受访者
最直接跟深圳有关的,是2022年,她上传了一张之前打工的食品厂大厅的照片,那是她的朋友发给她的。“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打工的厂,好怀念。” 工厂距离现在的工地二十公里左右,七八年过去了,她没有再去一次。
曾立新想念的不仅仅是老家的瓜果蔬菜。她的朋友圈全部可见,但也只有2018年到2019年有更新,仅仅8条朋友圈其中有5条是云南的菌子,2条是和家人的合影,都是图文并茂,菌子的照片都是还未采摘时候,在泥土里透出脑袋的模样,家人合影的背景是绿树瓦房和阳光。
2018年1月20日更新的一张照片,是南山区的高黑白高楼和伸向填空的塔吊,路边的蓝底白字标语格外亮眼“掌握安全生产只是 争做遵章守法………”这个动态没有文字、没有定位,是她第一次做塔吊指挥拍的照片。
2018年11月20日,曾立新更新朋友圈,并配文“这是我们云南大山里山珍!有想吃的朋友吗”
除了刚来时候爬了大南山,曾立新再没有去过深圳的其他地方玩过。
她们人在深圳,但在最私密的自留地里几乎看不到深圳;密密麻麻的宿舍里住的都是人,她们有事却从不往外说。在这座城市里,她们是工地的筋骨,各自扛着生活,并排站立却无法触及;她们又像水,能够适应任何形状,情感和思念流向家乡,日复一日。
工地没有假期,工人一般的工作安排要六点左右起床,如果不加班的话下午6点下班,吃饭、洗漱。到了晚上9点,工地生活区的走道上几乎没人走动了,大部分人已经休息。
她们的生活范围就是围墙里的待建的工地。我们问她,来深圳这么多年,觉得有什么变化吗?李七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不太知道。
2022年3月30日,李七双发图并配文“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打工的厂,好怀念”
“留守儿童反而更好”
左正秋在2013年的时候跟着丈夫一起外出打工,刚开始在三亚,丈夫在工地做重工活,她带着孩子在工地住。孩子越来越大,到了上学的年纪,跟着大人奔波换班级,成绩越来越差;工地生活枯燥没有同龄人陪伴,左正秋的女儿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声点,所有人都在睡觉别说话。
渐渐的,她的女儿和儿子也不闹着跟在父母身边了。直到她的女儿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左正秋没有送过女儿去过一次火车站,也没有去过她的校园看看,她说,有些遗憾,但“没觉得亏欠,把他带到身边生活更多苦,留守儿童反而对他们更好”。
左正秋的室友之一蒋真已经45岁了,是在工地干活的第一年。她老家是贵州山区的,20岁就和老公来到深圳摆摊卖菜,卖了20年,直到去年儿子录取大学。这些年,他们一家在深圳租房子定居,儿子在深圳上幼儿园、北师大附中,大学去了黑龙江读书。
她的手粗壮粗粝,指甲剪短到肉里,手指上还有菜刀划下的伤痕,在风吹日晒成黝黑的皮肤添了一丝肉色。这双手一天能剥一大脸盆毛豆米;能在2分钟里把几十斤菜从地上裹走撂在电动三轮车上立刻开走,从城管的眼皮下飞速溜走。
蒋真很自豪地给我们看儿子初高中的照片,“从幼儿园开始,我就开始教他学习。后来辅导不了我都在旁边监督他学习。”卖菜起早贪黑,每天提心吊胆”,好在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儿子放学后,她就让丈夫一个人卖菜,她回家看孩子。“学习最重要,我在他旁边看着总好些。”
北师大附中的很多学生家庭优渥,每次开家长会蒋真都能看到很多好车。“我们的条件肯定比不上别人,儿子从小到大没有上过补习班,一直告诉他好好学习。”去年,她的儿子被哈尔滨理工大学录取,她觉得“自己的担子轻下来了”,不再卖菜,进工地打工。
蒋真还有两个23岁的大女儿和21岁的二女儿,一个专科,一个没考上大学出来打工。从小放在老家给公婆带。谈到这,她叹气诉说着自己的无奈,“感到对不起女儿,但是我没办法。”
“如果我进厂打工,更没法把孩子带在身边。”
梦断踏乡途
来到龙华这个工地前,我们曾在深圳南山区的另一处工地沉浮了半年。能取得她们的信任互相联系本就十分艰难,现实又缠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最后全部再无音讯。
去年9月,我们在工地加上拉作的微信,第二星期跟她连线的时候,她说,她离开深圳了,“回老家了,不回深圳了,很累”,再也没回来。
我们期待着和尤云霞一起从她的老家回深圳务工,在微信上互相发完新年祝福后,她告诉我们,家里要装房,等装修好再去打工;时间未定,地点未定。徐香玉的老公得了重病,回家了;葛雅丽的儿媳妇生了,她留在老家带孩子了……她们流动着,有人新来,有人刚走。
这种流动性和漂泊感,是农民工身上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但对女性来说,更沉重的是,她们身上还背负了家庭的枷锁,她们是照护者,照护丈夫,照护孩子,是家庭里最容易被牺牲的人。
杨承兰家两个女儿早已独立分担家庭开销,常劝她不要这么辛苦。房子装修需要钱、女儿的嫁妆要攒攒……她的人生课题好像很多,一直不能歇下来。
而今年9月,李七双和丈夫将会踏上回乡的路。这条已经坐了十年的列车第一次在春节外的时间搭载二人。
15岁的大儿子即将上初三,他们希望回到家乡,陪伴孩子,让他专心学习。做下这个决定后的某一天,有个亲戚去李七双婆婆家家串门,当亲戚问李七双的大儿子“你爸妈在哪里?”时,向来腼腆的大儿子一改沉默,大声地告诉亲戚:“我爸妈出去了,不过他们九月份会回来的。”
提到这里,李七双笑得暖心:“你说我们挣钱不都是为了小孩吗?孩子嘴上不说,心里高兴呢。”
左正秋的车停在工地旁边的公园里,有空的时候就会开车去找朋友玩。一开始开车来打工只是为了回老家方便,来到深圳后看到繁荣的网约车市场,左正秋又为自己谋划了另一条路。
这几年她陆陆续续去考了网约车司机证,但没有过。那就继续考,左正秋这样想,总要找事情做。“一个人闲下来,就好像等死一样。”
深圳又跳过了春季,在三月底直接进入30度的夏季。太热了,曾立新又想着。她的亲戚告诉她云南老家那边也有塔吊指挥员的活,“我可能明年就回老家了,但是——
谁知道呢,先干着再说吧。”
(除李七双、杨承兰、杨承银,
其他人物均为化名)
如有新闻线索或有意转载
请通过微信公众号后台私信编辑部